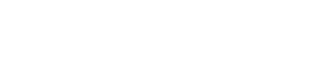讲述人:刘莉妮,2001年起在武汉大学从事国际中文教育工作至今。主讲中高级语言课程及中国国情与文化课程。分别于2006年和2009年赴韩国交流访学,2012年至2014年赴法国西岱大学孔子学院担任公派汉语教师。
武汉大学的东门,在东湖绿道的一端,正对着402路公交车站。这个僻静的校门,不似珞珈门、弘毅门、凌波门那样总是人来车往热闹非凡,它偏安一隅,日日迎接武汉大学的第一缕阳光,呼吸着东湖的澹澹水波吹送的清凉。
从东门进来,顺着扬波路一直往上走,经过“外招”那座白色的四层小楼,再下一个平缓的小坡,就到了武大的枫园。枫园和东门的气质绝配,它远没有樱园或梅园那样的鼎鼎名气,几乎看不到游人在这里拍照打卡,但对于武大的留学生而言,这里一定是最有记忆点和归属感的地方,是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家”。在静谧的枫园深处,在珞珈山温柔曲线的合抱下,国际教育学院静静地伫立着。几十年寒暑更替,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来来去去,在这里生活、学习,感受中国。离开时,他们都已把一部分的武大刻画进自己的生命,而枫园的每个角落,都留下了他们鲜亮的身影和成长的足迹。
清红
2019年8月,正是珞珈山里蝉声最盛的时候,武大校园里出现了一个清凉的身影。一袭长及脚踝的绛褐色长袍,面容清秀脱俗,眼神温和沉静。她是一位来自越南的出家人,俗名叫阮氏清红。
清红7岁时,看了一部中国电影《少林寺》,便被影片中僧人的勇气和慈悲深深打动,从此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佛法的种子也埋进了心里。两年后,9岁的小清红立志毕生弘扬佛法,父母尊重她的选择,送她去寺庙剃度出家。所有知道的人都感到不可思议:一部中国电影居然对一个越南孩子有那么大的影响,以至于成为她皈依佛门的缘起。提起这个,清红每每自己也会笑起来,然后很明确地说:是的,这是我和中国的缘分,和佛法的缘分。
在越南有个说法:不知道《西游记》的故事,一个人就没有童年。清红非常认可这句话。她从小就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的一切都感兴趣,而寺庙生活、前辈僧尼、佛家经典都让她有很多机会接触到汉语和中国的历史。在寺庙读完小学和初中后,清红去了河内更大的寺庙,继续读高中和大学,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她开始系统地学习汉字书写、汉语阅读、古琴、茶道、书法等。她的汉语老师是位从武汉大学毕业的越南姑娘,从老师那里,清红第一次听说了黄鹤楼、宝通寺、武当山。在她心里,这都是些闪光的名字,虽然还没去过武汉,但她对这座城市的亲近和向往日益加深。
2019年,清红终于获得了一个能来中国留学的机会,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武汉大学。行走在珞珈山的青翠林间,端坐于枫园教学楼的中文课堂上,清红度过了一学期愉快的时光。她喜欢武汉大学每一个温柔而安静的角落,享受着老师们热情而认真的授课,以及课后和中国朋友做饭、喝茶的美好瞬间。除此以外,她还实现了一个古琴的梦。
高中时,清红就爱上了古琴,她认为这种古老的乐器正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高中毕业,她买下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张古琴。虽然琴并不太好,但对贫寒的高中生来说,这把琴花光了她半年的生活费。来到武汉以后,清红认识了一位越南古琴高手阮延俊博士。阮老师同意收清红为徒,但是只教十天。十天之内,清红学会几首基本入门的曲子,如《仙翁操》《阳关三叠》等。至于她最想学的《流水》,阮老师笑着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现在的功力,还学不了这个曲子,你先认真练习两年后再说吧。”
清红以出家人的认真勤谨来践行老师的要求,自那天开始,她每天必定有两小时来练习古琴,不管是在武汉还是在回到越南之后。跟着网上的视频,她学会了《关山月》《神人畅》等曲子。不懂之处,她就一遍遍反复听、反复琢磨、反复练习。一学期结束后,清红回到越南过春节,没想到疫情暴发了。当初不支持她去中国留学的住持师父说:“你看吧,让你去美国学英语你不肯,非要学汉语,现在你回不去中国了,汉语学习就只好中断了吧。”清红不服气,她努力申请到了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在第二个学期以及第二年都能继续参加武汉大学的线上课程。除了诵经、礼佛、坐禅、抚琴,清红克服时差、网络等困难,把全部的休息时间都用来坚持学习汉语。住持师父被感动了,特别允许她在网课时间不用参加寺庙的活动,专心听课。清红也分外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2022年的秋季学期,有一次课间,我本打算给同学们播放一首中国歌放松一下,清红主动提出:“老师,我会弹古琴,我可以为大家演奏一曲。”她用手机对准自己拍摄,在同学们的期待中,清红开始拨动琴弦。那曲子时而清澈流畅,时而风急浪涌,一气呵成,气象万千,正是那首当年阮老师不肯教的《流水》。一曲终了,全班陶醉,可惜不能当面表达赞美,大家就在线上课堂的聊天框里拼命送花、热烈鼓掌、点赞。课后,我满心佩服感动,发信息祝贺她:“清红真棒!你果然在两年后学会了《流水》,这是怎么做到的?”清红发来一张截图,是古琴演奏家乔珊老师在Youtube上的表演视频,观看记录显示,清红看了27000遍!

与古琴为伴的越南留学生清红
清红离开武汉时,阮老师送给了她一张自己亲手制作的精美古琴,清红如获至宝。如今回到越南的寺院,清红仍然是一袭宽袍大袖,她从武大的盛夏蝉鸣中走来,走在越南灵单寺的小路上,只是背上多了那张阮老师赠予的古琴。她常常被邀请去表演中国古琴和茶道,一有中国游客参观,她就忍不住从禅房出来,用汉语跟他们聊上几句。直到今天,她还是每天随身揣着三年前武汉大学发给她的那张校园卡。前不久,清红打电话告诉我:
“很快,等我处理完在越南寺庙的事情,我就会回到我的第二故乡武汉。余生,我希望在中国度过。”
Kim
和Kim的第一次见面,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武汉大学在法国的合作孔子学院第一年招生,组织学员们来武大进行为期两周的游学春令营,由我担任这个短期班的汉语老师。十几位学员中,优雅的老太太Kim是其中的一位。
一次课间休息,其他同学都出去了,教室里只剩下我和Kim两人。
“Kim,你为什么学汉语,你或你家人是不是来自中国?”看她温婉的东亚面孔,我们开始闲聊起来。
“不对。老师,你猜我出生在哪里?”她饶有兴致地反问我。
“你叫Kim,是不是来自韩国?”她笑着摇头。
“那么,越南?”听她的汉语发音中约莫带有一点越、泰或两广一带的口音,我这样猜测。但她也说不对。
然后她告诉我,她是出生在柬埔寨的华人后代,父母双方的祖辈中,都带有一部分的中国血统。她十几岁就去了法国,在法国已经生活了近五十年了。
“所以我汉语不太好,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来学习。汉语是我的祖先的语言,我应该好好学,”她继续说,“我在法国,法国人一看我的脸,就想我是中国人。现在我来到了武汉,中国人一跟我说话,就想我是外国人,他们不想(不认为)我是中国人!”她在努力用刚学会的句型表达,语气渐渐激动起来。
“现在我不知道我是哪里人,我没有家乡了老师!”说完这句话,她突然悲从中来,眼睛里顿时盈满了泪水。她深深埋下头,把脸捂在厚实的大围巾中,“呜呜呜”地大哭起来。
本来是轻松的课间闲聊,却画风突变。面对着一位长者悲伤的眼泪,我手足无措,又意外又抱歉,只能赶紧走到她身边,默默递上纸巾。她柔弱的肩在我的双手间剧烈抖动着,我俩一时无言。此时,陆续有同学走进教室,Kim也迅速地调整了自己的情绪。接下来的时间,直到春令营返回法国,我们再没找到合适的机会交流。至于那天她为什么会那么伤痛,这个疑惑也就留在了我心里。
六年后,我被武大外派到巴黎的孔子学院任教。一走进高级班的教室,我就在众多好奇的目光中感受到一双笑意盈盈的眼睛,她先认出了我。原来是Kim,她竟然还在孔子学院坚持学习。他乡遇故人,真是个大惊喜。更令人欣慰的是,她的汉语跟六年前相比进步了很多,她对汉语学习的热情也有增无减。
高级班的课每周一次,Kim从不缺课。她家在大巴黎郊区,来一趟孔子学院不太方便,开车或坐火车单程都要一个多小时。我到孔院工作的第二年,她搬离了郊区舒适的别墅,住到了小巴黎,离孔院只要十来分钟,她非常满意这个决定。没有课的日子,每天一起床,她先做一套早操,然后用整个上午复习和预习汉语课的内容,一直到午饭时间。后来听说她调整了顺序,起床后先学汉语,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体力不够,如果先做完早操,就没有力气再学汉语了”。
她是有多么爱学汉语呢?有一次她给我展示了一个本子,里面全是她的中国朋友或汉语老师发给她的电子邮件。她把这些汉语邮件一字一句地抄写下来,再反复认读。大部分汉字都被标上了调号,有的词还备注了词义。看着她工整的字迹,听她如数家珍地朗读其中的语句,我又吃惊又感动,还有一点惭愧——本子上也抄录有我的邮件,可有些内容我都已经淡忘了。对我们来说,用汉语回复一封邮件,并不需要费多少时间和脑筋,但她却如此珍视,全都拿来作为汉语学习的材料。现在我再问她,你为什么那么爱学汉语?Kim这样回答:“因为汉字很美,汉语也特别好听。我听汉语就好像听到我爸爸说话一样。”Kim的父亲不会说普通话,只会说潮汕话,但是这不影响她感受汉语课带给她的亲切感。
日常她最爱跟人念叨的是:“你们年轻人啊,应该对中国政府温柔一点,不要总是批评!中国的发展已经很快,你们应该理解中国政府,这么大的国家,不容易啊,就像一个妈妈要照顾那么多孩子一样……”她总是耐心而认真地说这些话,语音语调不甚流利,却让人备感真诚。
圣诞节时,Kim一定会邀请孔子学院的中国老师去她家过节,年年如此。中国老师换了一批又一批,几乎每一位都受到过她的盛情款待。她说,法国人在圣诞节都要全家团聚,你们在法国孤孤单单,没有家人在身边,那就来我家聚一聚吧。Kim有一手好厨艺,尤擅东南亚风味。每个去过她家的人都会赞美——餐具雅致、食材讲究、摆盘艺术,每个菜都很隆重。她是真正把孔子学院的老师当作亲人来对待了。
在和Kim的接触中,我越来越感受到她的可爱可敬。人到暮年,能长期坚持汉语学习的,大多不带什么功利性目的,也正因为如此,才能克服困难坚持下去。担心会触及到她的隐痛,我后来没有直接跟Kim提起过几年前那次课间插曲,但答案也似乎逐渐清晰——尽管她出生在柬埔寨,生活在法国,一生中没有在中国长居超过两个月,但在她心中对自我身份的归属,始终是中国人。她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走过的那么多地方都是异乡,只有中国才是她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