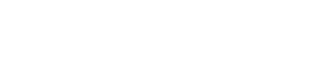讲述人:董锦程(Elliot O’Donnell),博士生,来自英国伦敦,2016年度武汉大学十大珞珈风云学子。2020年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单波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硕士论文《一个概念的旅行:基于中西方“后真相”研究文献的比较分析》,在CSSCI刊物发表论文《否思“后真相”:基于李普曼舆论学视角》。2021年在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工作一年,担任科研助理,在CSSCI刊物发表论文《“后真相”的旅行:一种比较分析的视野》。2022年至今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做中国哲学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师从吴根友教授,在CSSCI刊物发表论文《英国维多利亚时期道德经译本及其序言初探》,在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第17辑)发表论文《森舸澜的自然主义诠释学述评》。目前已发表学术论文4篇,参与省部级以上项目3项。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各种讲座、会议、论坛活动中负责组织工作并担任学术口译。参与的社会活动包括:陪同武汉市委前宣传部长李述永女士赴英国剑桥大学进行演讲《愿我们成为知音》;武汉电视台国际马拉松(武汉站)电视直播双语解说员;武汉电视台《家在武汉》节目主持人;武汉大学国际文化节双语主持人;感知中国“智汇珞珈”博士论坛会议主持人;ChinaFit健康营养与蔬食论坛讲师等。
作为一个西方人,我大概会不可避免地将东方复杂化和神秘化,这当然包括我对中国持有的预先认知。正是这样一个东方学的梦,让我以一个逃离者的姿态闯入一个未知的世界——这里是神龙与凤凰的起源,老子和庄子的故土,太极与气功的发祥。这里的生活方式与我过去的生活方式如此不一样。它在吸引我的同时,也在更新我对现实世界的每一寸感知。
一、走进螳螂拳
十二年前,一句汉语也不会的我离开了伦敦,从泰晤士河畔前往一个山海相依的东方圣地学习中国传统武术。我在中国的头两年,是在最质朴的乡村里度过的。大山和森林成为了我的朋友,和我一起接受训练的伙伴们成为了我的家人,我的师父给了我一个伴随我一生的汉语名字——董锦程。
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体。由于文化与思想的创造最终都可以回归到人皆有之的身体,身体似乎是一个可以被用来认知和理解不同文化思想传统的通用解码密钥。我童年的大部分课外时间,似乎都在为自己塑造出一个强健的身躯而努力。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玩橄榄球。对于橄榄球这种运动来说,绝对的力量是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身体的理解很不一样。在中国,阴阳哲学被编码到了很多运动中,比如螳螂拳。万事万物永恒变化之法则,在螳螂拳的套路中得以呈现。
我透过萨义德的镜片去看螳螂拳,它加强了我心中那个模糊的、深不可测的东方幻象。作为一种非竞技性运动,螳螂拳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绝对的胜者或败者,其终极衡量标尺,是一个人的意识与身体在多大程度上得以结合。事实上,我们的身体总是遵循着心灵的路径,这让我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及内在环境需要发生改变。
我对中国的整体理解,被昆嵛山那种萨贺芬式的轮廓塑造成形,它让我与中国之间建立起一种充满复杂感情的浪漫关系。回到伦敦度过了一段短暂时光之后,我决心从大学退学,重返遥远的东方追求一个更高层次的教育。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一次,我选择了另一个山水相依的地方,开始了我漫长的求学之路。
二、从语言到哲学
如果说昆嵛山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在珞珈山的经历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时间毫不留情地掠走了我的花样年华,却让我对知识的追求变成了一种永恒的信仰。
我习惯凌晨四点起床读书,无论寒冬酷暑,这个习惯伴随了我整整十年。对我来说,学习汉语并没有那么困难。因为在语言上取得的快速进步,我在大三那年与中国媒体和娱乐行业有过一些亲密接触。这样的接触和交流虽有价值,却不是我想走的路。在一个追逐10W+的流量时代,我更想在一种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中寻找意义。
本科毕业前,我去广州参加了一次朗诵比赛。直到比赛当天,我们才知道除了朗诵环节之外,还需要进行才艺表演。为了给武大争得荣誉,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穿着西装和皮鞋表演了一段螳螂拳,随后从感知中国文化的具身视角进行了一段即兴演讲。
这并不是我发挥最好的一次演讲,但它引起了台下一位评委的兴趣。面对面的交流总是最好的,这位善良的老先生邀请我和他共进午餐。他使用的语言和概念完美地捕捉了我在昆嵛山对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感受和体验,在我心中播下了中国哲学的种子。若干年后回顾这场奇遇,我才知道那天和我娓娓而谈的竟是大名鼎鼎的成中英老先生。
当汉语变成了我文化身份的一部分后,我迫不及待地想从学术视角重新审视自己从现实中获取的知识和感受。幸运的是,引领我走入学术大门的是学界享有盛誉的单波教授。
与老师初遇,我还不知道学术为何物。幸蒙恩师言传身教,得以渐渐开悟,让我的学术之路不再是一个未知的梦想,而是有了一个踏实的起点。
老师一直鼓励我远离浮躁,静心读书。他开放包容的胸怀、谦逊豁达的态度以及为学为人的品质,一点点渗透到我的治学道路上。记得第一次和老师见面的时候,老师问我,“你的学术野心是什么”。答曰,“实现自我解放”。虽然现在的我远没有实现“自我解放”,但毫无疑问的是,老师赠予了我一把宝贵的钥匙,让我逐步打开桎梏心灵的一道道枷锁。
读书对我而言,不仅是为了求知,更是一种修行。老师对我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他让我义无反顾地去走他曾经走过的那条路——哲学。
三、两位汉学家
我逐渐开始了解一个真正的武汉大学。每一个夜晚都有那么多的讲座,到处都是求知若渴的学生。跨文化的思维在这里相遇、碰撞,却又宽容对待彼此,呈现出真正的和而不同。这三年,让我再一次深深地爱上了武汉大学,且是日渐浓烈的爱。春日樱花雪月,夏日万木葱茏,秋日枫叶彤彤,冬日红梅傲雪。珞珈山下的各个园子,有灯光的地方就有书声朗朗,伴随着四季花香、夏蝉冬雪,对一个爱书之人来说,人间仙境也不过如此。
硕士第一年的圣诞节,我在伦敦的Waterstones书店里看到一本书Taking Back Philosophy: A Multicultural Manifesto(哲学上的拨乱反正:多元文化哲学宣言)。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著名汉学家Bryan Van Norden,他在这本书中对欧美学界的哲学民族中心主义进行了条理清楚的反驳。
读完这本书,我和我的邻居Mirsky先生进行了一次愉快的讨论。Mirsky是改革开放之后最早一批来华访学的西方学者。他和我住在一个街区,这个街区还住过一位中国著名文人,老舍先生。年逾八旬的Mirsky已有许多年没有重返中国,他对我在中国的经历总是充满了兴趣。每次回到伦敦,Mirsky都会请我吃饭,邀我去他家喝茶聊天。他的书房里塞满了与中国有关的各种书籍,这些书浓缩了他一生的学养和志趣。也让我意识到,我目前在中国的一切经历,终将有其意义。
五个月后,我将Van Norden教授请到了单老师的读书会上。这位令人敬重的汉学家以其谦和朴实的长者之风和长者之德深深感染着我。他非常相信哲学就是对话,这里的对话是双方真诚的阐释和具有建设性的回应;其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寻找真理,一个是个人修行。这次读书会之于我,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起点——作为对话者,我第一次在中国和西方学界之间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
四、对话
疫情暴发的那个冬天给了我难得的闭关修行机会,我在封城的那100天发表了人生的第一篇C刊。
武汉解封之后,珞珈山向我发出召唤。我在半山庐的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度过了一年时光。这是一段平静而诗意的居住,珞珈山的这个角落远离了樱花的招摇,也远离了世俗的喧嚣。走出小小的办公室,走廊的尽头有一个天台,守楼的阿姨在那里种了很多花花草草。那一年的天台经常咖啡飘香,坐在石凳上背诵《道德经》,成为了我的中国哲学入门。
从本科到博士,我一直感受着武汉大学浓厚的跨学科研究氛围。无论是跨学科还是跨文明,始终落脚于对话。
和我遇到的其他所有老师不一样的是,吴根友教授从未将我视为一个外国人。他一方面给了我最自由的学术氛围,一方面对我提出了最严厉的研学要求。这一年也是我学术汉语突飞猛进的一年。作为文明对话高研院的科研助理,我协助吴根友教授组织了很多讲座,做了很多学术口译,也用汉语写了很多新闻稿。这份工作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中外著名学者,印象深刻的学术活动如复旦大学白彤东教授、山东大学贝淡宁(Daniel A. Bell)教授与吴根友教授的全球文明视野下的政治模式三人谈、中山大学梅谦立(Thierry Meynard)教授的晚明清初中西哲学汇通的三种尝试,程虹教授的文明与质量跨学科对话、张昌平教授的三星堆与中国上古文明记忆学术访谈、一带一路视域下的文明对话研讨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传统文明的转换与发展学术研讨会等等。
学术之路是孤独的,但我的研学之路并不孤独。武汉大学文理学部山多路曲,我在珞珈山的林间小道上留下了一路深深浅浅的脚印。
五、万有引力
从2013到2023,我从青葱年少走到了而立之年。这是我一生中最美的年华。不乏波澜,却收获颇丰。
十年间,我用脚步丈量了中国的大好河山,感受了绵延千年的历史遗产。我穿行过独库公路,跨越过河西走廊、环绕过塔克拉玛干,造访过青藏高原;曾在色达佛学院看天葬,在五台山徒步登台,在喀什古城漫步,在中国四大石窟朝圣;无论是北上内蒙古高原,西至可可西里,还是南下胥家港湾,就算被带到天涯海角,宇宙的边缘,最后我都会回到珞珈山。
珞珈山是我的起点,我的灯塔,我的第二个家乡,我的万有引力。这座山不及昆仑巍峨壮观,不及峨眉旖旎秀丽,但她见证了我的青春,我的梦想。珞珈于我,是深深的执念——是我的过去,我的现在,也寄托着我对未来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