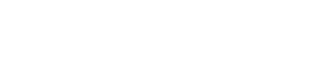讲述人:杨巍,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阿拉伯语专业,1996年入职武汉大学,曾于2000年受国家汉办派遣,前往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从事汉语教学工作,为期两年。
千禧年
从高中开始,我就时常憧憬21世纪的壮观气象,偶尔也会想象千禧年时自己是怎样的模样。
“到2000年,我就该27了。要是我能考上北外的话,说不定就真的是一名外交官了!”那时的我很乐观。“杨巍,大学就考北外,上外也行,毕业后到外交部去。”初中时英语老师随口跟我说的一句话,成了我后来努力的方向。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切似乎在一瞬间就都揭晓了答案。
1992年,我考上了北京语言大学,读的是阿拉伯语专业。尽管是“北语”,而非“北外”,可对于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娃,能去首都上大学,这一字之差又能有多大的遗憾呢?只有激动与兴奋。
1996年,我又荣幸地入职武汉大学,成为一名对外汉语教师。
那时,对外汉语教学行业还默默无闻,我所在的单位在武大校内也完全不起眼。当被问及所属院系时,如果说的是“经管院”“计科系”,闻者必然连连点头,可当我说出“留办”两个字时,对方几乎都会愣住,一脸疑惑:“留办”是什么?“留办”的全称是“外事处留学生事务办公室”,怎么听都不是一个教学单位,所以即便我把这名字说全了,也没几个人能猜对我到底是干什么的。
2000年,千禧之年,我获得了出国任教的机会,去的是位于北非的突尼斯,任期两年。
上世纪末,由教育部派往国外任教的汉语教师人数非常少,主要从教育部直属高校中选拔,每年也就遴选一百多人,能被选上很不容易。我申请的是突尼斯高等语言学院中文系的岗位,当地通用阿拉伯语和法语,而我有阿拉伯语专业背景,这个确实比较稀罕,所以第一次申请就幸运地获得了外派的机会。走出国门,中学时的愿望也算部分实现了吧。
那年,我27岁,结婚才两年。现在回想起来,当初一门心思去争取这个赴外工作的机会,抛下亲人只身离开,是很自私的选择。而自始至终,我的妻子、父母、岳父母都给了我最无私的支持和鼓励。
小企鹅
如果能穿越回20年前,你最想带过去的一件东西是什么?我的选择是一部智能手机,或者一台笔记本电脑。当然,网络必须得跟过去,那我就还能发朋友圈,还可以QQ聊天,可以刷抖音。
2000年,笨重的台式电脑在中国都还谈不上普及,所以我踏上非洲大陆时,自然是两手空空,没有电脑,更不要说手机。但是,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QQ用户,我有一个5位数的QQ号码。那时,小企鹅其实还不叫QQ,它叫OICQ。我把OICQ的安装程序存在一张3.5英寸软盘中,带到了突尼斯。我乐观地认为,有了它,即便走遍天涯都不怕。
作为非洲大陆数一数二的经济强国,突尼斯的首都给我的第一印象远好于我的预期。街道干净整洁,市民亲切友好,生活物资丰富,市内还建有轻轨,生活十分方便。所以,安顿下来后,我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就只有一个:找一台能上网的电脑,把我那可爱的“小企鹅”给装上。
于是,我开始四处寻找网吧。这活儿挺累人,为什么呢?因为我基本上是走着去找的。突尼斯的物价真不低,为了省钱,我能不坐车就不坐车。初到异国他乡,凭着好奇心、新鲜劲儿,加上现实的需要,多走些路虽然累,但不是什么问题。最初那一两周,只要一有时间,我就跑出去转悠,一边找网吧,一边探索这座异域城市。
找到一间网吧并不难,毕竟这里每年要接待数百万来自欧洲大陆的游客,旅游相关的基本设施都不缺。但是,要找到一台对中文友好的电脑,却似海底捞针。突尼斯没有一家网吧的任何一台电脑装的是中文版的操作系统,而且大部分电脑无法安装我带去的小企鹅程序。
天无绝人之路,我一家一家试,一台一台装,终于在市中心的一家网吧内找到了一台可用的电脑!尽管整个过程中弹出的所有窗口都显示不了汉字,取而代之的是一堆乱码,但我凭着电脑菜鸟的勇气,一路试错,最终成功地让小企鹅在右下角闪烁了起来!狂喜之下,我点开妻子的头像,键入一行拼音:Beijing shijian jintian zhongwu 12:00 jian !!!
那天夜晚,我实现了到突尼斯后与妻子的第一次网上相会。尽管看拼音比较费事,但我俩真的好开心,似有说不完的话。小企鹅跟着我们又叫又跳了三个多小时,直到夜深了才被迫下线。
狡兔得有三窟。只找到一家网吧的一台电脑可用是不够的,它不专属于你,也不确定能用多久。于是我掏出小本儿,又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将脚力所及的所有网吧中的可用机位一一记录了下来。东边不亮西边亮,得确保通讯无虞。
某天晚上,我走出网吧,夜空中飘着细雨,风已经带有寒意。与往常一样,街道上早已空无一人。夜色正浓,只有昏黄的路灯作伴。我拉了拉外套的拉链,低头快步往回走,住处在4站路之外,说远不远,说近不近。走着走着,眼泪竟涌了出来,猝不及防。
凤爪
赴任之前我就被告知,因为我是新增派的老师,突尼斯那边并没有前任教师留下的房子可住,需要我到任后自行租房居住。面对这个情况,我这没有外派经历的新手老师心里肯定是忐忑的:搞不好要露宿街头啊。好在经有关部门联系协调,我得以先借住在已到任的老师家中,我有两周的时间去给自己找房子。
租房倒是不难,找一家租房中介公司,委托他们去办就好。中介带着我看了三处房子,前后一周多时间就搞定了。拎包入住,并没有多少故事可讲,难忘的是那一周多的“借住生活”。
好心接纳我借住的是来自我母校的N老师,他比我提前一个多月到任,接下了前任教师留下的住房。N老师50多岁,和蔼可亲,对我友善又热情,还爱跟我说话,加上北语的这层关系,让我毫无寄人篱下之感。
住下的第二天,N老师带我去附近的菜场买菜。一路上,他跟我详细介绍了当地各种蔬菜、海鲜、牛羊肉的价格,跟北京的价格一一进行了比较:“西葫芦便宜,所以我常买西葫芦……这儿的带鱼是真新鲜!鳃都是鲜红色的,还不贵……大虾也好,手掌那么大个儿,在北京你根本吃不起……牛羊肉都太贵,我一般不买,就吃鸡肉,鸡肉便宜……”
说话间,N老师带我来到了一个卖鸡肉的摊前,他指着摊位旁的塑料桶问摊主:这个多少钱?摊主面无表情地伸出一根手指,答道:1第纳尔。N老师弯下腰,把那一桶东西全都倒进了我们带去的大袋子里。这下我看清了,那些都是剁下的鸡爪子。
“凤爪可是好东西,这里人不吃!我头两回来的时候,都不要钱,直接就给我了。看我来得多了,他们也学精了,每次都管我要1个第纳尔。”N老师很得意地跟我说。
“那还是划得来,国内可不便宜呢。”我脑子里算了算,1个突尼斯第纳尔差不多值5块人民币,这一桶有好几斤。
回到家,N老师就带着我处理这一大堆鸡爪子。要不是有这段难得的经历,这处理鸡爪子的手艺,恐怕我一辈子都没机会学。
因为我们拿回来的都是未经处理的原材料,带着硬皮,粘着不可言说的附着物,跟国内菜场或超市里出售的干干净净、白白胖胖的凤爪相比,观感上相去甚远。所以呢,整个过程只可意会,不宜细细描述。
一通有味道的操作之后,N老师将收拾好的凤爪分装成四五个袋子,放进冰箱的冷冻层。“这些够咱们吃一周了!”看着N老师开心的样子,再看看一地的狼藉,我用胳膊拭去额头的汗,长吁了一口气。
借住在N老师家的一周多时间,我们每天的菜谱基本都是西葫芦炖凤爪,外加一个青椒炒土豆丝,或者西红柿炒鸡蛋。每次开饭,N老师都要说这么一句:“西葫芦炖凤爪,这个菜好啊,蛋白质、胶质、维生素都有,又有营养又便宜,做起来也方便。”那一阵子,我特别希望N老师哪天能心血来潮,换个口味,折腾一盘卤凤爪出来。
后来,我搬去了自己租的房子,紧挨着上课的学校。再后来,N老师为了上课方便,也搬到了我的住处附近。我俩课后仍然往来密切,成了忘年交。
一位父亲
突尼斯与中国相距遥远,各领域的交流从规模上看都比较小。在突尼斯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人,包括中国大使馆、中资公司、中国医疗队等各类组织机构,加在一起也不到100人。因此,通过大使馆组织的一些活动,比如国庆招待会、新年团拜会等,大家很快就建立起了联系,有些就交上了朋友。
我认识了突尼斯乒乓球队的金教练。金教练当时30多岁,说着一口沪式普通话,是世界冠军王励勤在上海队时的队友。这次,他跟突尼斯体育部签了个聘用合同,过来执教他们的乒乓球国家队。金教练也是一个人过来闯荡,所以我们时常互相走动。每次他率队出国比赛归来,都会带一些外国的啤酒、食品回来,然后叫我们这些朋友过去分享。而当他需要写训练计划或者总结的时候,我们也会帮他做一些翻译工作。
我认识了江西援突医疗队的李医生。李医生为人宽厚实在,在我们这群人中年龄最长,扮演着大哥的角色。和我一样,他也爱好打篮球,所以经常组织大家搞一些体育活动。因为有李医生在,我们谁有个头疼脑热的,心里就不慌。
我认识了广州某公司驻突办事处的小叶。小叶比我还小三岁,这么年轻就被公司派来驻外,独当一面,必有其过人之处。小叶有车,方便时就经常给我们当司机。他开车带我们去专门的屠宰场买猪肉,带我们去临时集市买适合国人口味的大米,带我们去郊外参加各种文娱活动……
我认识了沈阳某公司驻突分公司的裴总。老裴和他夫人住在一栋豪宅里,院里停着两辆豪车,一看就知道这家公司在突尼斯的生意做得不小。老裴夫妇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照顾有加,经常招呼我们跟他去野外钓鱼,钓完就去他那儿打牙祭,吃完还让大包小包往回带,搞得我们都很不好意思,但心里是真开心啊!
我们这群人,机会合适时也会相约一起出游。突尼斯并不大,我们走遍了老城,在最繁华的大道上来回踱步,我们在最负盛名的蓝色小镇喝咖啡,在迦太基遗址上的斗兽场内听音乐会,我们跑到最北端的比塞大港口眺望意大利,我们也曾组团深入撒哈拉沙漠探访《星球大战》的拍摄地……
多年以后的一天,当我翻开相册,沉浸在对过往的回忆中时,却突然发现,其中竟然没有一张N老师的照片。在突尼斯的那两年,我和N老师的交往要远多于其他人。可是,每次我们有外出游玩的计划时,N老师却总是婉言谢绝与我们同行的邀请。这真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
我合上相册,忍不住打开微信,向一位相熟的北语老师打听N老师的近况。
“哦,杨老师你还不知道呀?N老师已经走了好几年了……他这一辈子太苦了……”朋友一连回了我好几条,跟我说了些N老师家里的事。看着看着,我鼻子一酸,眼泪模糊了双眼。
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傍晚,N老师晚饭后来到我的住处,给我送来他新收到的几份报纸。那时,每位外派老师都可以免费订阅两份国内的报刊,我跟N老师是一起商量着订的,这样可以交换着看。所以,我俩隔三差五就会互访,送个报纸,聊聊天。那天,我正要出去散步,就邀他一起。跟以往一样,N老师又推脱不去。
“我真不明白,您怎么那么不喜欢散步呢?反正这会儿也没事,就跟我一起出去走走吧。”我忍不住想说动他。
“你走得远,走的又都是石子路,费鞋。”N老师笑了笑,指着他的脚说,“不怕你笑话,我脚上这双鞋穿了有6年了,还好好儿的。爱惜点儿穿,我就不用在这儿买新鞋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奇怪的“费鞋”说,“该换鞋就换呗,又花不了多少钱。”我不解地问。
“你们年轻人讲究这个,我们年纪大了,没那必要,换个新鞋还硌脚呢。”N老师依旧笑呵呵的。
因为西葫芦和鸡爪子便宜就顿顿吃西葫芦炖鸡爪子,因为怕费鞋而不愿跟我去散步,因为舍不得花钱几乎从不与我们一同出游……这些印象叠加在一起,让我对N老师产生了一个刻板印象:极度抠门儿。甚至后来我离任回国后,在与朋友们谈起这段经历时,还把这些拿出来当段子讲,博人一笑。
听了北语的朋友跟我讲的那些N老师的事,我真有抽自己俩耳刮子的心。原来,N老师唯一的孩子有先天的缺陷,独立生活能力差。他出国前曾跟同事说:“孩子其实离不开我,但我没得选,我得抓住这个机会,毕竟出国教书能多攒下点儿钱。我这把年纪了,没别的念头了,就想着给孩子多留点儿钱,到时候我跟他妈能走得安心些。”
我很惭愧,这么多年一直以自己的浅薄去揣测一位伟大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