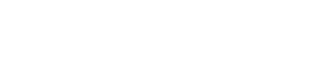讲述人:萨尔波塔姆·什雷斯塔,来自尼泊尔,199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医学院。先后担任中尼友好组织尼泊尔阿尼哥协会主席、副主席,以医生身份积极推动中尼文化交流,推进“一带一路”事业。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是86版《西游记》尼泊尔语版译者,此外还翻译了多部中文纪录片和文学作品,撰写了二十多篇介绍中国文化的文章,发表在尼泊尔不同报刊。
1987年秋,我在北京语言学院完成了一年的汉语进修课程,便坐火车去了武汉。我将在那里学习临床医学专业。到了武昌火车站,我意识到,我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就要开始了。时任湖北医学院留学生科科长的章光彬老师带着张志强老师到武昌火车站迎接我们。原来,乘坐同一趟火车到武汉来读书的还有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只是之前我们相互不认识。
学生们到齐后,章老师就在火车站开始点名。外国人的名字一般都很长,我的全名也很长,姓和名字加起来有九个汉字,相当于三四个中国人的名字。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章老师把我的名字的九个汉字准确无误地叫了出来,他还把我父母的职业都说得很准确,章老师一定非常认真地做了功课。
那时候,整个中国的外国留学生都不太多,武汉的更少。当年武汉市所有大学外国留学生全部加起来可能不到一百个。在湖北医学院的外国留学生,包括我们八七级的,总共就二十个,但为这些留学生配备的辅导员、会计、厨师、保安、清洁工等等加起来可能也有二十个吧。
我们到学校后的那几天,医学院院长等领导还接见了我们。不久,留学生科来了一位名叫周富生的新老师。他比章老师和张志强老师都年轻许多,章老师就像我们的长辈,而周老师像我们的兄长。周老师的出现使留学生科的氛围比以前更活跃了。包括留学生的私事在内的所有事情,他都很热心帮忙,而表扬和保护我们留学生是他一贯的作风。
我们虽然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了一年的汉语,而且在那里的学习成绩很不错,自我感觉也良好,但来到湖北医学院,开始跟中国学生一起上课后才发现,自己还没有过语言关。虽然班里的中国同学们很热心,都很愿意帮我们,也确实帮了很大的忙,但同学们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他们自己也要学习。
了解到外国留学生面临的语言困难,留学生科给大家安排了汉语辅导课,这才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的问题。留学生科准备为我们开办两年的汉语辅导课,但到了第二年级的下学期,我们大多数都觉得语言已经不是大问题了,请求停止了汉语辅导课。
留学生科的老师们都特别关心我们的学习,除了给我们安排汉语辅导课,还跟许多教研室的老师打了招呼,请他们给我们准备一些容易看懂的笔记,或每次上完课留几分钟的时间给留学生讲一下当堂课的重点,或跟我们交流一下我们是否听明白了。这种做法对我们非常有效。
在留学生科的请求下,人体解剖学教研室的张友云老师专门为我们编出一本近百页的人体解剖学重点笔记。中国同学们见到张友云老师为我们编的笔记后都非常羡慕,因为借助这本笔记书,本来很难学的人体解剖学变得容易许多。我后来听说,张友云教授因为对外国留学生的这种特别关爱,被评选为优秀教师。
病理学教研室的舒清波教授是一位非常关心外国留学生的老师。每次上实验课他都关注着每个留学生的状况。他要求我们上实验课的时候不要换位置,每次都坐在同一个位置上。开始我们不明白,他说:我是搞病理形态学的人,位置或定位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原来他不是用名字记下我们,而是用我们的位置来记的,而且他的这种记忆很可靠。原本不太在意考试成绩的我,竟在舒老师的驱动下学得格外刻苦,他教授的病理学课,我考出了全班数一数二的好成绩。
中南医院(当时叫湖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普通外科的史海安教授也是特别关心外国留学生的一位老师。只要他在病房或科室,都会主动过来跟我们留学生谈论外科学的问题,总会教我们一些新的内容。虽然他的提问式的交流经常让我们感到紧张,但我们还是很喜欢听他讲,因为他在这个时候讲的内容尤其珍贵。
一次我正在普外科实习的时候,史教授跟科室的其他几位教授讲:我想让他(指我)考我的研究生,你们觉得怎么样?一位教授立即回答说:“不行,他当不了外科医生,他动作太慢了。他呀,适合当内科或儿科医生。”史教授当时没有说什么,但他并没有因为其他教授的否定而改变他的想法。两年后,我的尼泊尔同胞在普外科实习的时候,史教授跟他谈起此事,遗憾地说:“我很想让他考我的研究生,但他却考了神经内科。”我们研究生毕业典礼上讲话的时候,史教授又提了此事,典礼结束后我的研究生导师余绍祖教授跟史教授讲:“感谢史教授,您割爱把塔姆让给了我!”
轮到骨外科实习了。骨外科的很多老师给我们讲过大课,但之前没有机会与老师们有更多的接触。在骨科实习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机会。当时中南医院骨科学领域的显微外科做得比较出名,陈振光教授是杰出代表,他设计了显微外科的一些新型手术。我对这些新鲜事物非常感兴趣。有一次,马上要进行一台新型手术,我问带课老师,可否上手术台观看。老师说手术时间很长,本科实习生不要求参加,如果真的想去观看当然没有问题。就这样,我也穿上手术衣,近距离地观看了几台显微外科手术。那些都是新型手术,全世界才做过几例,每次手术期间都有人来照相。
几天后我在校园碰到陈振光老师,他还专门问我是否拿到手术台上的照片。陈教授竟然还注意到了我,我感到很惊讶。第二天,我问带我的老师:“那几次手术,陈教授怎么会注意到了我?”带我的老师是陈教授的研究生,他说:“显微外科手术耗时很长,我们是陈教授的研究生,可我们都怕,你一个本科实习生,在手术台旁边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一动不动,看得那么认真,所以陈教授注意到你,还问你的情况呢。”当时我想,动作慢,又没有魄力的我,如果想搞外科的话,也许显微外科是一个选择吧,因为显微外科要求医生的动作特别精细、轻柔。
康复科是我比较喜欢的另外一个科室,我喜欢康复科的一个原因是我对针灸学的兴趣。针灸学在中国归于康复科。实习的时候我选康复科就是为了多学点针灸学。在康复科实习期间,我开始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另外一个瑰宝按摩学产生了兴趣。当时医院康复科针灸室和按摩室两科室挨着,在针灸室实习的时候我会偶尔进到按摩室看看。徒手按压也能治病?刚开始我并不相信,当我开始随访一些病人,得到他们的肯定后,我决定减少针灸室的实习时间,到按摩室去实习一段时间。
一个外国留学生对按摩学产生兴趣,并到按摩室去实习,当时按摩室的主任医师田辅友老师特别高兴,特别重视对我的培养。他常说:“很多中国人都认为按摩只是放松身体的,不是治病的,但我可以告诉你,按摩能够解决许多问题!”他希望我在那里的时候好好学习,离开中国后就没机会了,因为其他国家没有中国按摩学。为教我按摩学,田辅友老师还好几次叫我到他家里,单独给我教授一些知识和手法。
田辅友老师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非常丰富。一次他讲到按摩的“滚法”手法的时候说,这是滚水的滚,如果想体会水是怎么滚动的,你可以到长江边上去看看。长江离学校不远,我到江边去认真观察了好几回江水的滚动,体会到了水的滚法。没过多久,我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的《推拿学》教材上看到提手旁的“㨰法”。田老师那么强调是“滚水”的滚,书上怎么是提手旁的㨰呢?有一天我就问了田老师,他笑着说,一个外国人还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但他坚持说,传统上还是滚水的滚字,提手旁的㨰字是近来才创造出来的,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
1992年,我本科毕业后考上人民医院神经病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的第一导师是余绍祖教授,具体带我们的第二导师是李承晏教授。到了研究生阶段,很多情况都变了,我就不用转很多科室了,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的科室和实验室,每天打交道的人也是一样的,这样不久自己也变成了科室的一员。
在医学院、中南医院和人民医院,喜欢我们,关心我们这些外国留学生的老师和工作人员绝不止这么几位,还有几十甚至几百位,这里无法一一讲述。我们留学的那个年代,中国的开放程度还没有现在这么高,但我在武汉的那八年,从没有因为自己外国人的身份遇到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在学校的八年,一直都不是那么轻松,大家知道医学专业要学的课目非常多,临床医学这个专业本来也不是容易读下来的。本科毕业后我读的神经病学的研究生是研究型的而不是临床型的,所以三年读研究生期间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科学试验。本来没有临床经验的我,在研究生期间积累临床经验的机会也不多。研究生毕业典礼的时候,余绍祖教授送了我十四本有关临床神经病学的中文和外文书籍,重得我都无法用双手托起。我把余教授的这个礼物理解成:三年的时间主要用于科学试验,临床经验还远远不够,回国后自己学习,自己摸索吧。
在校时忙于学习,毕业回国后才开始回头看自己的所学。跟南亚各国毕业的医生朋友交谈中发现,中国的科目比他们的多一倍。他们的本科课程像寄生虫学、病理生理学、核医学这样的课没有单独设为一个科目。中国很重视这些专业内容,所以把它们设为单独的科目来教授。跟他们不同的另外一点是,其他国家的课程安排是培养一位单纯的临床医生,他们并不重视科学思维的培养,而在中国培养临床思维和技能的同时,也重视科学思维的培养。
研究生时期这种特点更为突出。当时导师余绍祖教授特别嘱咐我一定要上《自然辩证法》这门课。因为他认为,在临床上有时候只应用医学思维和经验不够,还要应用哲学思维,《自然辩证法》这门课程对培养哲学思维帮助很大。在临床医学科学和自然哲学思维问题上,中国毕业的医生比其他国家毕业的医生有明显优势。有时我想,我毕业回国初期的那几年,没有进入国家医院、医学院或其他大医院工作的情况下,在小诊所行医并能够生存下来的主要原因,就是这种医学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的能力。
我在武汉读医学的另外一个特殊收获是中国传统医学知识,这一点我在上边也提到过。虽然我没有办法把中医药用于尼泊尔日常的行医工作中,但针灸和按摩我一直在用。针对一些神经系统疾病和多种疼痛症,按摩治疗仍然是我的首选治疗法。所以,每当我想起刚回国时那几年的逆境,我都相信,帮助我最终逆袭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把我所学到的中国传统医学的知识,成功地应用到了诊治病人的实践中。
在武汉读书期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条中医名言是:没有治不好的疾病,只有没本领的医生。我从这句名言中受到很大的鼓舞。虽然在医疗实践中存在绝症这样的事情,但它的范围一直在缩小。绝症范围的缩小也是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回国开始行医后,我始终将这句名言铭刻在心,竭尽全力治病救人。在诊治病人时,将中国传统医学和其他医学知识相结合的想法和勇气也是从此开始的。我想,在我刚回国的那几年中,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我都咬牙坚持了下来,这其中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的这种信念吧。
从武汉大学毕业回国后,我时常想,是中国和武汉大学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应该如何报答中国和武汉大学?作为武汉大学培养的一个外国学生,我想到的报答方式有两个。一个是作为武汉大学培养的医生,我绝不能给我的母校丢脸。中国的医学领域的三个方面,临床、科研和教学一般是平行的。但我毕业回国后,因为多种原因放弃了科研和教学这两个方面,一心一意地只做临床工作。我在科研和教学方面没有任何成果,但我相信作为一个临床神经内科医生,我绝对没有给母校丢脸!
我认为报答中国的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给我的国人“讲好中国的故事”。我曾在中国学习生活九年,后来也经常去中国,所以我认为我有资格讲中国的故事,也有义务和责任讲好中国的故事。虽然在大学里正式学习的是医学,但我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时候,我亲眼目睹了那个令世人惊叹的日新月异的中国。
除了亲身的经历以外,在章光彬老师的教导下,我对中国革命史和当代政治也有一些了解。我还记得到武汉的第二年,学校为我们留学生安排了一次长途旅行。到海南通什市(现在已经改名为五指山市)的晚上,其他同学都去跳舞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宾馆呆着。带我们去的章光彬老师看见我一个人没有去跳舞,就过来问,我说我不喜欢跳舞。当时我看章老师也有空,就跟他讲:“我想了解中国现代历史,中国同学们上的中国革命史那些课程我也很感兴趣,但没给我们留学生开这门课,您能给我解决这个问题吗?”章老师说:“让你去跟中国同学们一起上政治课不太好办,要不我给你上中国现代史、革命史如何?”从那天起,章老师就开始给我讲中国现代史、革命史,时间不定,一般一个月一两次,没有固定的教材,不是正式上课的那种,而是想到哪里讲到哪里,或者我提问他回答。这种学习持续了五年,直到他退休。我毕业后从尼泊尔回武汉探望他的时候,他每次都会提前准备好给我的学习资料。如今网络发达,他每天还在通过微信给我转发一些值得了解的文章和新闻报道。
我认为自己有资格讲中国故事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也有一定的研究。在这方面我的同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在武汉大学上学的时候,课间经常有同学主动过来跟我谈中国古代文学。他们会讲,已经学会中文的一个外国人,如果不去学唐诗宋词的话,那真的是一辈子的遗憾。我相信他们的话,虽然我当时没有办法系统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但我开始收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书籍。在武汉读书八年,我收集的书籍有一千公斤,搞得毕业时把那些书籍运回尼泊尔变成了一个大工程。那些书籍中,一半以上是有关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书籍。
回国后的十多年我忙于为自己的生存打基础,从2012年我开始为讲好中国的故事投入不少时间和精力。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做中文的翻译,围绕中国问题、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进行写作。在校期间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产生的兴趣现在终于可以发挥作用了。
《人民日报》的一位中国记者曾经报道过我的情况,主要介绍我利用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些治疗方法治好了不少病人,获得了尼泊尔人民的好评。这篇报道赞扬我将中国传统医学推广到尼泊尔主流医学界,推广了中国文化。实际上,这也是我用自己的方式在讲中国故事,回馈武汉大学对我的培育之恩。